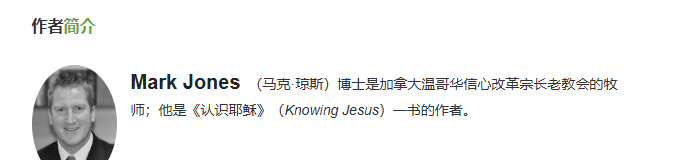作者:马克.琼斯(Mark Jones) 译者:小草
这篇文章是关于《现代神学精髓》(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的一些富有争议性的问题。
1。《现代神学精髓》(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的作者爱德华·费雪(Edward Fisher,1627年 – 1655年)有个有趣的历史。约翰-特拉普(John Trapp,1601年 – 1669年)称他是一位狡猾的反律主义者。先不说 “反律主义者 ”这一部分, 关于“狡猾 ”这一部分是怎么回事?
请看查德·范·迪克霍恩(Chad Van Dixhoorn,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撰写的这篇出色的挖掘历史的文章:
“在我看来,费雪几乎肯定知道审查反律主义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及其活动,他似乎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调整,以避免他们的责备。费雪对新教改教者和前几十年的清教徒作家的引述颇为大量,在书的开始几页插入了数目不寻常的引言,这些引言的作者都是议会的反律主义者成员、如约翰-莱特福特(John Lightfoot)、和爱德华-雷诺兹(Edward Reynolds)。此外,他只引用了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作者,即弗朗西斯-罗斯(Francis Rous),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对反律主义者提出指控的国会议员。费雪仅在 1645 年版《现代神学精髓》的结尾处,巧妙地在一两页中提到了被指控的反律主义者约翰-伊顿(John Eaton)和托比亚斯-克里斯佩(Tobias Crispe)。在他的 1646 年版本中,他狡猾地删除了对他们的所有提及,以冗长的独白取代了对话的这一部分,并增加了对威斯敏斯特神职人员的引述。”(见《序言者特维斯(Twisse)奇怪的沉默:威斯敏斯特议会关于称义的辩论中的预定和政治》,《十六世纪杂志》40 (2009),第 395-418 页)。HT: Patrick Ramsey.
近年来有更多的研究揭开了费雪的背景。我们需要记住,尽管他有着班扬式的才华,但他并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神学家。
2。 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 1676年 – 1732年)缺乏神学训练和图书馆资源,这对他理解十七世纪背景下的《现代神学精髓》有何影响?
我不确定波士顿是否能够很好地理解在他前一个世纪的文本,因为他根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有这些资源。比如,如果他能多读一些普雷斯顿(John Preston ,1587年 – 1628年 )的著作,他肯定会得出普雷斯顿是一个假定普救主义者(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t)的结论。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很少批判前几个世纪那些人的历史神学。我认为我们假定他们是对的,而没有进行必要的挖掘,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仔细阅读过。只要读一读约翰-波尔(John Ball)的著作(1645 年)的序言,一些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承认他们太忙了,没有仔细阅读他的著作,但他们还是推荐了这部著作!万变不离其宗。
3。与上述第 2 点相关,不断变化的史学似乎表明费雪是一个假定普救主义者(hypothetical universalist),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结果?
我知道波士顿和他的朋友们并不认为《现代神学精髓》教导假定普救主义。许多学者竭力回避这一想法所隐含的意思,但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否认《现代神学精髓》教导的是假定普救主义(HU)。
英国的假定普救主义者在他们关乎福音的白白的恩典背后有作为牧者的考虑。费雪在《现代神学精髓》一书中引用的 Culverwell 的观点与福音的白白的恩典有关, Culverwell 是持假定普救主义的立场(Ussher说服了他)。据我所知,在这点上,改革宗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特定论者(particularists)都不会对费雪所使用的语言感到舒服。后来苏格兰的特定论者对费雪的语言并没感到不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节点。
因此,当讨论与《现代神学精髓》相关的白白的救恩的性质,以及围绕这一主题的所有教牧问题时,我们对苏格兰《现代神学精髓》争议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将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现代神学精髓》教导假定普救论主义(HU)。
4。精髓人(Marrow Men ,译注:赞同《现代神学精髓》观点的人)是否对赫尔曼·韦修斯(Herman Witsius, 1636-1708,译注: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和其他人)感到舒服?
著名的《奥赫特拉德信条》( Auchterarder Creed)中写道:”为了来到基督这里,我们必须离弃罪,这样的教导既不正确也不正统。” 1716 年,奥赫斯特拉德长老会给出了一系列提议,要求候选人在按立为牧师时必须同意这些提议。信经中的这一提议旨在防止一种预备主义。
苏格兰教会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认为这句话是 “不正确和可憎的教义”。
因此,精髓人为了捍卫《奥赫特拉德信条》,最终打了一场仗。但是,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过去的改革宗神学家是否肯定一个人要归向基督必须放弃罪?
有趣的是,所谓的中间人赫尔曼·韦修斯(Herman Witsius)在十七世纪后期出现的反律主义者-新律法主义者的争辩中,问道,悔改是否在赦罪之前。
对罪的忧伤(悔改)是否先于称义,“作为一种处置条件,主体的前提”?
韦修斯宣称,圣经的简明性比“学派的微妙”更为可取。
当圣灵将新生命的原则注入罪人里面时,拥有这种恩典之灵的人身上就会发生各种属灵的行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被圣灵催促 ”的灵魂会看到自己是污秽的,而基督是满有恩典的。当这发生时,人就会对自己不满,并逃向基督。“因此,开始接受基督,从污秽和罪孽中被救出”。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因此,结论是,如果没有之前的悔改,或至少是相伴的悔改,以及新生命的目的,我们就无法相信,我们是藉着信接受基督为义“。
换言之,韦修斯认为,一个醒悟的罪人在接受基督之前(或同时相伴),在他的经历中,有一种对罪的憎恨和新生活的目的,这是 “正确和正统的”。
精髓人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吗?这是他们的对手所说的一切吗?关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至于后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了(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
信心先于称义,悔改也是如此。韦修斯认为,悔改是恩典之约的特权;但悔改是上帝要求罪人的责任,是 “作为一种行为来执行 ”,”为了得到赦免,而不是悔改赚得赦免。。。是表明有效的呼召和被重生。。。”
还有魏司坚(Geerhardus Vos,又译霍志恒,1862年 – 1949年)的观点: “没有认罪,就无法想像相信,而且,相信基督在真理的光照下是合理的,而不是一种盲目的、神秘的冲动。因此,按顺序来说,悔改和对罪的认识是先于降服的信心,这是毋庸置疑的。“
5。当今质疑《现代神学精髓》,不会被指控为 “狡猾的新律法主义 ”吗?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 David Como, Jonathan Moore, Aaron Denlinger, Donald John Maclean, William Vandoodewaard, Richard Snoddy, Michael Lynch 等人所做的出色的史学研究,意味着这类问题不是新律法主义者的疯言疯语,而是在关心真实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事情。
波士顿对恩典之约的条件性有所保留,但我所读过的正统改革宗神学家,几乎都肯定恩典之约的条件性(如,Davenant 主教;另见《清教徒神学》第 19 章)。傅格森(Ferguson)认为:”然而,后来波士顿有很不同的想法: ‘我对恩典之约的条件性之说没多大的好感’ “(第 67 页)。 波士顿还说:”我不是很热衷于把信心称为条件。。。”
我所研究的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们在描述信心如何是接受圣约的益处的先决条件时非常谨慎。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防止反律主义所认为的信心不是接受基督的益处的条件。
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虑;事实上,上述问题只是《现代神学精髓》的极其复杂的历史的一些皮毛。
— 译自《The Marrow: Some Questions》